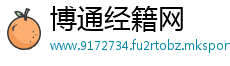这只盔犀鸟(Helmeted Hornbill)正在将果实带给巢内的难拍家人。它和它的影师同类实在太难找了,我们差点就只能在杂志篇章里放别种犀鸟的差点照片。还好最后我们不需要用其他犀鸟的放弃照片,但这种鸟类实在太特别了,极危所以我们分享在这边。盔到摄 PHOTOGRAPH BY TIM LAMAN  摄影师提姆.雷曼在哈拉巴拉野生动物保留区高高的差点树冠层上搭了掩蔽帐,监看一棵结果的放弃榕树,希望盔犀鸟会来这里觅食。极危 PHOTOGRAPH BY TIM LAMAN  泰国南部哈拉巴拉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一只公的马来犀鸟正在吃榕果。 PHOTOGRAPH BY TIM LAMAN  菲律宾普林塞萨港地下河国家公园(Puerto Princesa Subterranean River National Park)中,一只白嘴斑犀鸟(Palawan hornbill)咬着一颗榕果。 PHOTOGRAPH BY TIM LAMAN, NATIONAL GEOGRAPHIC CREATIVE  这只双角犀鸟摄于泰国的考艾国家公园(Khao Yai National Park)。 PHOTOGRAPH BY TIM LAMAN, NATIONAL GEOGRAPHIC CREATIVE  哈拉巴拉野生动物保护区里,一只双角犀鸟在飞往结果的榕树途中,先暂停在雨林树冠层上整理羽毛。 PHOTOGRAPH BY TIM LAMAN 视频:从盗猎者手下拯救盔犀鸟的任务内幕 (神秘的地球uux.cn报道)据美国国家地理(撰文:Rachael Bale 编译:钟慧元):稀有的盔犀鸟太难寻找,让我们差一点点就得靠其他种犀鸟的照片充版面。 我们的盔犀鸟杂志篇章本来几乎连一张盔犀鸟的照片都没有。 好啦,这样说是有点夸张,但我们真的差点没有足够的盔犀鸟照片来填满杂志版面。当摄影师提姆.雷曼(Tim Laman)一开始决定要报导这种样貌古老的鸟类时,他就知道这会是个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这种鸟极度稀有、害羞且难找。 「我在东南亚的雨林里追踪犀鸟已经很多很多年了。」提姆告诉我:「我想继续追踪这个故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在我20年前的《国家地理》犀鸟篇章里拍了许多其他种犀鸟的照片,但并没有拍到好的盔犀鸟照片。」 不过,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刻都重要。盔犀鸟正逐渐步向灭绝,因为用它们的「头盔」雕成的雕件在黑市里炙手可热。其他犀鸟的盔突(它们头顶的角状物)是中空的,但盔犀鸟的盔突是实心的,很容易就能雕成珠子、小雕像和错综复杂的场景,而且突然之间就成了某些有钱中国人小圈圈里的热门玩意儿。 就我们所知,要拯救盔犀鸟还不算太晚。但要让大家关心,我们就需要将这种鸟最华丽的面貌展现在大众面前。 「我知道这一定很困难。」提姆说:「20年前就很困难了,现在它们被猎杀的数量又多更多,让这种鸟变得更稀有。事实证明这比我预期的还困难。」 提姆知道,找到盔犀鸟最佳的机会大约是从3月到8月,也就是它们的繁殖季。此时雌鸟会把自己封在树洞中孵蛋、哺育幼鸟,为时长达150天,在这段期间,雄鸟必须一天送好几次食物给它们吃。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个被盔犀鸟使用的巢,就至少有机会看到一只雄鸟。 我们联络了泰国的一个研究团队。他们雇用了过去的犀鸟猎人来监测并保护犀鸟的巢──他们是专家,知道哪些巢有被盔犀鸟使用,以及该怎么找到它们。 花了好几个月,就为了一瞥这种极为罕见、目前生存状态为「极危」的盔犀鸟。 结果等着我们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被犀鸟使用的巢穴,它们位于一座山顶上。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这是趟非常陡、非常泥泞、非常费力的跋涉,而且还要拖很多装备。提姆和我稍微算了一下,一共有15位挑夫,每人带18到20公斤重的装备,所以至少有270公斤重的东西被拖上山──包括营具、一个发电机、吃的、还有所有队员的旅行袋。而且提姆说,这些行李已经尽可能轻了,只带了《国家地理》摄影等级的必要器材:他的瑞德(RED)数位电影摄影机、几台Canon的单眼反射式相机、一套镜头组、重型三脚架,还有一个比较轻的三脚架。 我从来没有这么感恩自己是作家,只需要纸、笔和用来观察写作主题的双眼就好。 我们一抵达第一个筑巢地点,提姆就帮我们搭好可以躲在里面的掩蔽帐,接着我们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等着犀鸟爸爸带食物给配偶和雏鸟。我们常听到它颠狂的笑声,仿佛就在几棵树之外嘲笑我们。或许它是在摸清楚靠近这里到底安不安全。完全符合它的学名Buceros vigil,因为vigil的意思就是「警觉的」,无论我们藏得多好,它似乎就是知道我们在那里。 不过,它还是现身了几次,但时间实在太短,想要拍到《国家地理》等级的照片真的是一大挑战。 观察了几天的鸟巢以后,我们听说附近的哈拉巴拉野生动物保护区里有一棵榕树正在结果。这是我们在不同环境里见到盔犀鸟的机会。榕树结果的时候,整个森林里的动物都会去大快朵颐,所以我们一定要尽快到那里去,才能在树上果实被吃光光之前,找到饥饿的盔犀鸟。 我们抵达时,刚好刮起一场暴风雨,但提姆还是设法在附近树上的高30公尺处搭了一个掩蔽帐。谢天谢地他没有被雷打到。 第二天早上和之后几个早晨,我们都清晨五点一过就到榕树那里。我们希望如果能在太阳出来之前就先就定位,盔犀鸟就不会知道我们在那里。 坐在清晨的黑暗里,提姆高高在上,而我在地面,我们听着夜行性昆虫逐渐安静,日行性昆虫开始嗡嗡作响。在我们等待的时候,夜雾逐渐消散,换上白天的湿气。我们看到了猴子和巨松鼠、马来犀鸟和双角犀鸟。但是,唉唉,没有盔犀鸟来吃榕果。 每天在树上待10个小时似乎并不会影响提姆。他很会把自己弄得舒舒服服的。 「我尝试要弄个小座位,」他说:「我有个小垫子可以坐,也可以四处移动、稍微伸展一下。虽然盔犀鸟不合作,不过还是有其他鸟类跟猴子。可以看的很多,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拍照跟拍影片。」 在榕树上待了几天之后,我们必须移动了。我前往印尼继续采访,提姆则回到第一个地点去看另一个巢。这个巢的雄盔犀鸟比较没那么害羞,他也终于能多拍到几张照片。不过还是不够多样。 「当时我唯一拍到的,就是鸟巢的照片:雌鸟已经在里面了,雄鸟在递食物给她。这很棒,但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提姆说。 回到办公室以后,团队开始讨论要凸显其他种犀鸟。如果我们就是拍不到足够的盔犀鸟照片……好吧,我们推论,那就表示这种鸟真的是行踪飘忽又稀有。整个犀鸟家族迷人又美丽,所以我们觉得,不妨也介绍其他几种犀鸟,以描绘东南亚雨林生态系的完整面貌。毕竟,我们也的确看到一些漂亮的马来犀鸟和双角犀鸟。 距离篇章刊出之前还有几个月时间,我们计画要再到印尼的婆罗洲一趟,那里是盗猎盔犀鸟的热点。我们希望,当我们在森林里的时候有机会看到盔犀鸟,但我们知道这一趟的重点,恐怕是在于纪录这种鸟遭猎杀的故事,而不是亲眼见到它们。提姆没有时间在掩蔽帐里连续待好几个小时了。在这趟旅程中,我们的希望不大。 跟原住民达雅人中的伊班族(Dayak Iban)相处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深入了解了这种鸟类在他们文化中的重要性,还有为什么有些族人会转而盗猎这种鸟。然后就在旅程的最后一天,我们从一位研究员那边听说,他的小组在婆罗洲西部看到一对盔犀鸟在勘察可能的筑巢点。 好得令人不敢置信。这是为我们的故事拍摄盔犀鸟的最后机会了。 我得飞回华盛顿特区,但小组的其余成员很快就准备好补给,满怀期待地朝那个地点出发。 「我听说这个地点的时候真的非常兴奋,」提姆说:「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能够在巢外拍到雄鸟和雌鸟。我非常开心──也松了一口气──能拍到不一样的照片,让整个故事能聚焦在盔犀鸟身上,这也是我们原本的目的。」 最终,提姆的坚持造就了一系列关于盔犀鸟行为的描写,包括一些从来没有影片记录过的细节。虽然我们最后不需要用到这些其他犀鸟的照片,但因为这种鸟类是如此美丽,我们希望能在此分享它们的照片。 |